潮汕美食之潮汕砂鍋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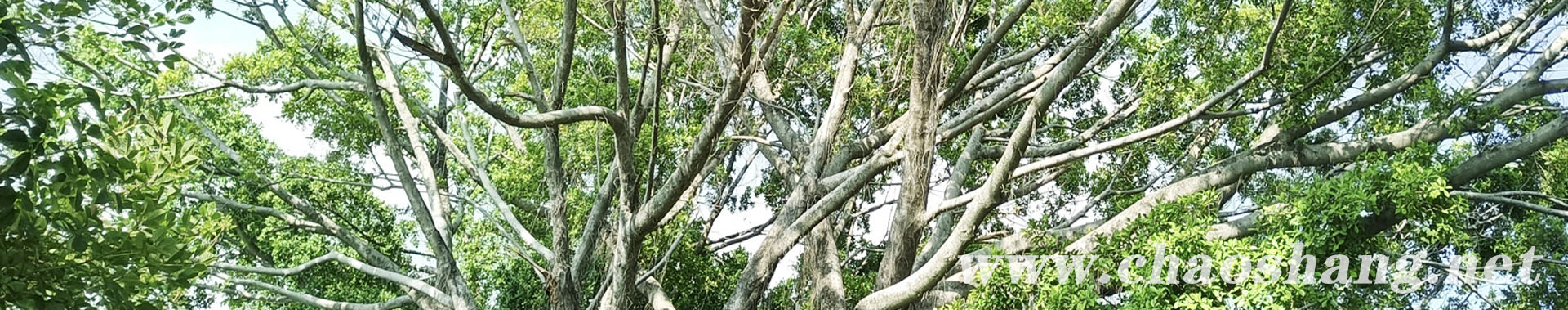
土神的祭祀,是種社區(qū)性的節(jié)日。潮汕人把這種節(jié)日俗稱為“營大老爺”。
這種節(jié)日起源于土地崇拜,上地崇拜導(dǎo)致土神的產(chǎn)生。土地之神,古人稱之為“社”,潮汕人則把它叫做土地公或者伯公。土神的祭祀,有兩種性質(zhì)。一種出于對所耕種的土地的崇拜,是對土地上生長五谷,供給人們食糧的報(bào)德;一種出于對所定居的土地的崇拜,是對土地營建鄉(xiāng)邑,保護(hù)人門安居的感恩。在亡古時(shí)期已經(jīng)是這樣。商代的甲骨文,就有“要不要向邦國的土神祈求豐年”的卜問(《前》4·17·3);近年在鄭州商代工城遺址發(fā)掘出一處以立石為中心的祭祀地,考古學(xué)家說,這是建城時(shí)祭祀土神的遺跡(裴明相《鄭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內(nèi)涵》)。在潮汕,伯公的祭祀仍然保留著這兩種性質(zhì)。上面提到的六月廿六引自公生,屬于前一種性質(zhì)。潮汕人建房子、創(chuàng)村寨要先拜伯公,屬于后一種性質(zhì),而鄉(xiāng)閭間在春日對伯公的祭祀,則兩種性質(zhì)兼具。例如:
《普寧縣志》載:
(二月)春社日,各鄉(xiāng)農(nóng)民具香帛、酒饌,相率祀其鄉(xiāng)之土神,以祈谷。祀畢,聚飲于神側(cè),曰“做社”。
《南澳縣志》也載:
(二月)二日,各街社里逐戶斂錢,宰牲演戲,賽當(dāng)境土神,名曰“春祈福”。
春日社神的祭祀,既有五谷豐登的祈禱,也有臺境安寧的冀求。在潮汕社會最基層的里社,社神大多就是伯公。
營大老爺是由鄉(xiāng)閭的伯公祭祀發(fā)展而來的。
鄉(xiāng)間社神的祭祀,本來只是一種宗教儀式,后來,由于在祭祀過程出現(xiàn)了某種社會組織形式,社祭本身也就開始有了其他的功能,這種發(fā)展,在南北朝時(shí)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。
《荊楚歲時(shí)記》說:
社日,四鄰并結(jié)綜,會社牲醪,為屋于樹下,先祭神,然后飧其昨。
可知梁朝時(shí)候,社祭之日,鄰里合會醵錢買辦牲酒祭品,先祭過土神,然后大家一起聚餐。社祭除了酬神之外,顯然也有了增進(jìn)鄰里團(tuán)結(jié)、加強(qiáng)鄉(xiāng)村治理的作用。于是,隨著歷史的發(fā)展,在社區(qū)的整合與擴(kuò)展的過程,產(chǎn)生了社祭和廟祀的混和,即在一個(gè)擴(kuò)大了的社區(qū)中,由某一座神廟承擔(dān)起社壇的功能。這座神廟所供奉的某一位神明也就成為這個(gè)社區(qū)的社神,潮汕人將它稱做“大老爺”。
潮汕各地的大老爺名目眾多。其中有進(jìn)入朝廷規(guī)定把典的神明,如城隍、關(guān)爺、媽祖等等;有佛道諸神,如南極大帝、玄天上帝、呂祖等等;更多的是民間創(chuàng)設(shè)奉祀的雜神,如三山國王、安濟(jì)圣王、雙忠圣工、雨仙爺、水仙爺、龍尾爺、珍珠娘等等。在一個(gè)相對獨(dú)立的社區(qū)里,各色名目的老爺按照其祭祀范圍的大小,被組織在一個(gè)有等級的系統(tǒng)之中。在鄉(xiāng)村,里社各有所祀的伯公,全村有共祀的大老爺;有些地方,相鄰的幾個(gè)村子由于行政上或者經(jīng)濟(jì)上的原因而有了密切的關(guān)系,也有數(shù)村共祀的大老爺。在城鎮(zhèn),街巷各有所祀的伯公,各坊有共祀的大老爺,而其上又有全城鎮(zhèn)共祀的大老爺。這些伯公、老爺?shù)募漓耄€保留著上古上神春祈的遺風(fēng),時(shí)間集中在農(nóng)歷年初,故潮汕有“營神正、二月”的俗諺?
營神的營,是潮汕方言詞,在這個(gè)短語里,它保留著回繞(《漢書顏?zhàn)ⅰ?和畛域(《文選薛注》)的古義。上神的祭杞而稱作“營大老爺”,是因?yàn)榧漓脒^程,必有土神巡土安境的儀式。照潮汕人通常的說法,營老爺分文營和武營兩種。在最基層的社區(qū),文營的做法,是在祭祀儀式過后。將老爺請上神轎,由選定的丁壯抬著,儀仗鼓樂前導(dǎo),巡遍社區(qū)的每一條巷子,再繞社區(qū)的邊界游行一圈, 回到神廠。武營的做法,一般只有鄉(xiāng)村社區(qū)才采用。祭祀儀式過后,要先用紅布將神像捆緊在神轎上,做好疾跑的準(zhǔn)備。營神開始,各條巷子的巷頭都燃起篝火。丁壯們抬起神像,飛奔來到篝火前,用力把神座舉到頭上,縱身跳過火堆,跑過小巷。跑完村里的巷子,又跑出田洋,抬著老爺巡游村界,回到神廠。潮汕人把這種做法叫做“走老爺”——潮州話的走,是跑的意思,這也是一個(gè)保留著古義的方言詞。不管是文營還是武營,其原始意義,都在凈土驅(qū)邪。不過,這一宗教儀式對于每個(gè)社區(qū),實(shí)際上又有著整頓社區(qū)秩序、強(qiáng)化社區(qū)治理的功能。
在營大老爺?shù)娜兆樱輵虺晟瘛@蠣敵鲅驳膬x仗隊(duì)伍,由標(biāo)旗、彩景、醒獅、歌舞、大鑼鼓、潮樂隊(duì)各個(gè)并不固定的部分組成,盡管由于社區(qū)具體情況不同,儀仗隊(duì)的規(guī)模可能差別甚大,但都充分展示了觀賞和娛樂的性質(zhì)。于是,坊鄉(xiāng)的這種土神之祭,毫無疑義地成為一個(gè)社區(qū)性的節(jié)日。
 |
 |
管理員
該內(nèi)容暫無評論